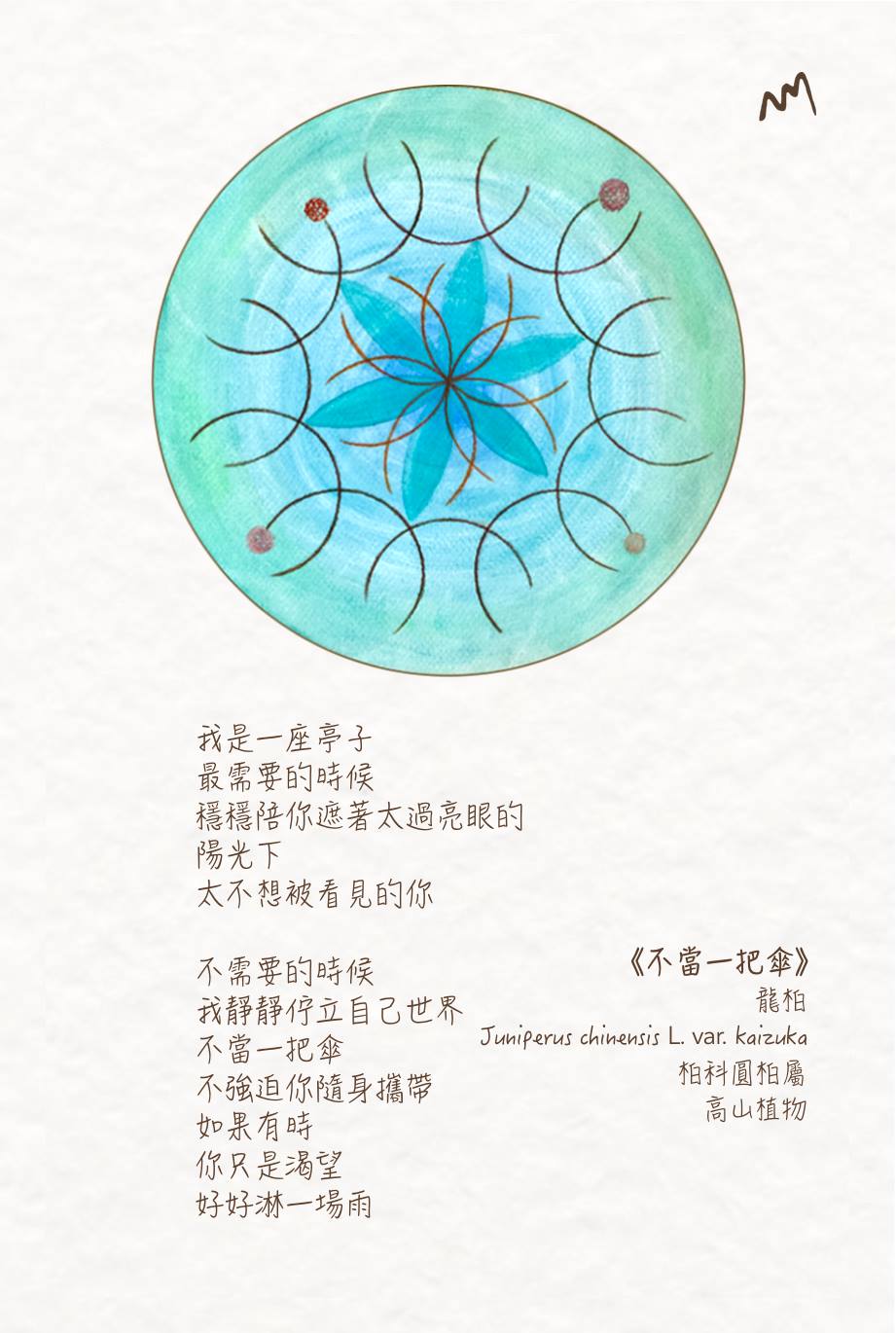東風回返大地解凍
文/吳星瑩
立春
一候東風解凍

華麗滿佈著花,五層樓高的巨樹。遠遠地,有一位中年婦女從樹下的人家走出來,緩緩爬上斜坡,一直走到我身旁,停住。
我們一起等著還沒有來的小巴士。
她看著我,我目不轉睛,看著巨大的花樹。
「好美的樹!這是妳家種的嗎?」終於,我捨不得地結束凝望。
「這棵老樹啊......至少有一百歲了喔!」她的尾音如此神秘,彷彿藏了很久以前的曾經。
「哇!妳怎麼知道啊?」明明那時她並未出生。
「我小的時候,它就跟現在一樣了!所以我想,它應該很老很老了......」
她的臉上浮現一抹小少女的微笑,樹老了,但盛開時仍如嬰兒。樹,是我能想像最溫柔的褓姆。
「妳就住在那裏嗎?」我指著露出一角的房舍,安穩歇息在樹的照拂下。
「不是!那是我媽媽的房子!我已經搬到山下去了。」
車來了,中年婦女上了車,轉頭微笑道了再見,好像是向我,又好像是向樹。
車走了,我輕輕凝望樹。花在風中搖曳,它在最美的時刻,迎回了它遠颺的少女。也許樹下屋裡的祖母,才是它最早守護的孩子,少女不再是少女,孩子也有了孩子。它看著一切逐漸老去,塵埃風霜,然而在它眼裡,無論何時相見,仍然是最美的時刻。
立春時節,和煦的東風輕輕吹拂,大地開始解凍,春天從此時開始。
一切總是會回來的。
總有什麼,在幾乎遺忘,不被期待的地方,努力履行著約定。
越走越遠,我們常常遺忘了感覺。生活像在不停追趕,一台總是提早開走的公車;又像在不停等待,一台總是遲遲不來的公車。我們交會在同一處站牌,錯落成規則的一直線,一張接一張倦意的面容,像不交集卻被迫連續的底片膠卷,不斷被編進身不由己的劇本,而自己的戲份,認不認同都要演完。
逐漸溶入一個城市的所有關係其實那麼微弱,如一台公車盪悠悠駛著,所有下車的人不會再回頭,知道有什麼就正要開走,可是沒有人注視送別。一片片模糊的身影,其實不是冷漠了,只是不停被裁走一段又一段,連自己也拉不住,於是無法再伸出手拉住,即將消逝的他人。
然而彷彿在最深處,有一個微弱的自己,仍在努力,不願看慣一個城市的天際線。
像無論走得多遠,有什麼仍然停留原地,仍然能夠守候,如一棵樹。
努力讓心底有一小塊角落,仍能綻放,仍能感動,溫度起伏、濕度升降、晝夜流動、行人走踏,那些生命中微乎其微的每個細節,仍然擁抱,仍然注視,像生命的每一分鐘,都有它的約定。
有些約定,從來不曾說出,但從來未曾打破。
一直,一直努力存在,就是一種意義。

.
.
.
.